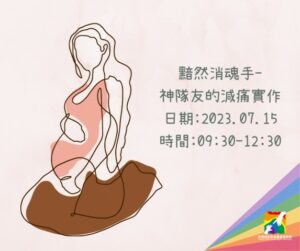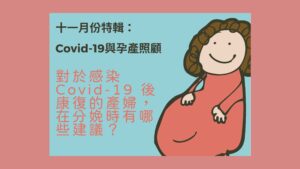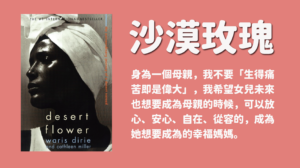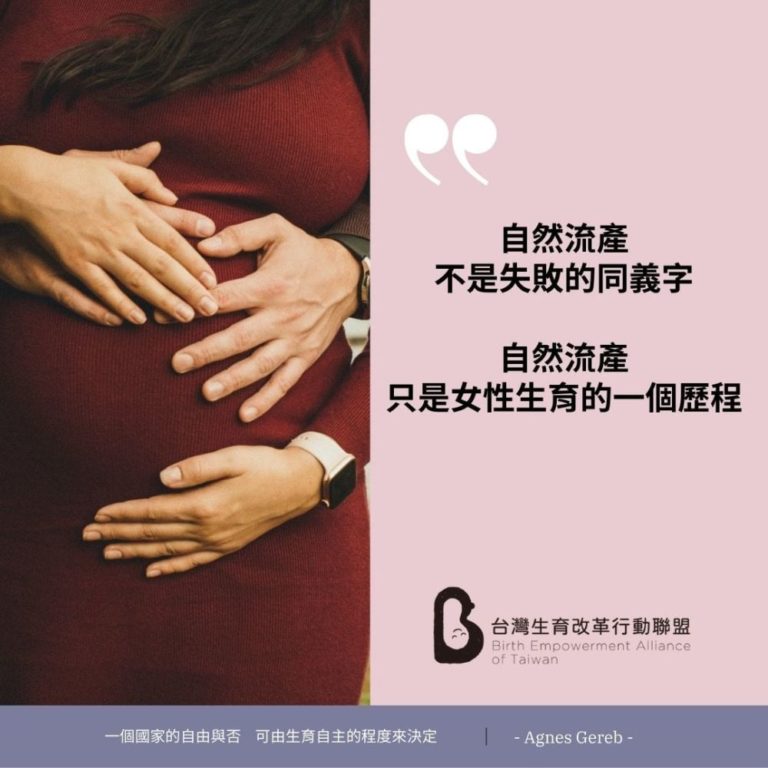圖文/施麗雯(生育改革行動聯盟理事、台灣蒲公英小產協會理事、臺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
經歷自然流產和死產的女性,在進入醫院接受醫療照護時,隔壁的產房的新生兒哭聲和孕婦的陣痛叫聲,可能會加深他們的悲傷與失落。
考量到這樣的情景,丹麥在2011年時,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率先區隔出兩間流產照護的病房,專門提供給流產的女性使用。因為得到許多正面的回饋,其他醫院的助產師也陸續來此參訪和學習。2021年後,首都哥本哈根的3間醫院(Rigshospitalet , Hvidovre Hospital 和 Herlev Hospital)先後設立流產照護產房。目前丹麥全國的23間醫院,已經有6間醫院的產房設有流產照護產房,由助產師主責照顧14周後的自然流產、死產和人工流產 的女性和伴侶。
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的流產照護產房
今年夏天,我參訪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幸運地認識當年提出流產病房概念的助產師Dorte Hvidtjørn(也是Aarhus University臨床醫學系的副教授)。
在她的介紹與帶領下,拜訪了這個丹麥最先創設流產照護的特別產房。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每年的新生兒人數大約是5000人,其中約有80個女性會需要使用到流產照護的產房。考量到流產照護需要特定的專業和訓練,所以在人力安排上,流產照護的的助產師是以12小時為輪班的設計。

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的兩間流產照護產房區與一般產房在同一層樓,透過走廊區隔開兩邊。要進入這區的產房是需要得到允許,才能從前門進入這區。前門與其他產房的走廊相通;後門可以直接下到樓下的院子,讓女性與伴侶保有一定的隱私。為的是讓這些家庭可以不受打擾地安靜休養、和跟已流產的寶寶或者悲傷相處。
產房的房間裡的牆壁上的圖畫、燈飾和一些擺設,源自設立時的巧思,希望透過這些溫馨小品來減少醫療化的感受。另外,與一般產房的小張單人床不同,在這的產房都是雙人床,用意是讓女性和伴侶可以一起臥躺在床上。Dorte也特別跟我解釋,雙人床擺置的重要寓意是照顧家庭,這邊的照顧對象不是只有流產的女性。
換言之,流產是一個家庭共同經歷的事情;而不是女性自己一個人的事情。
Dorte說,自流產照護產房啟用後,過去14年間,只有兩位女性是以剖腹產來進行流產,其他都是選擇陰道生產娩出胎兒/寶寶。「因為這是他們唯一可以為寶寶做的事情,也不會留下印記。」
醫療處理流產的部分後,出院的時間因人而異,住進來的女性可以自己決定想要待多久就待久。他們也可以選擇隨時看已流產的胎兒/寶寶,12小時輪班的助產師會因應其需求來提供照護。
Hvidovre Hospital的「蝴蝶牆」
2023年我和生動盟的監事吳嘉苓(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系教授)一起參訪了丹麥最大醫院Hvidovre Hospital的產房,接待我們的助產師Louise也特別帶我們去看流產照護產房。Hvidovre Hospital的產房在空間(隱私)的區隔、房間內部的燈光與擺設也都有特別的巧思。除了一張單人病床外,房間的另一個角落也特別放置了陪產者的床,目的是讓女性和陪產者在醫院期間都能夠好好休息。

妥善照顧流產家庭是醫產護人員的職責,但這些醫產護人員也需要有完善的支持系統才能承接流產家庭的失落與悲傷。Louise特別跟我們分享,主責流產照護的助產和護理人員一年會有四次的免費心理諮商工作坊,以確保提供流產照護的助產和護理人員得到妥善的心理健康相關資源支持。
除了對流產家庭提供醫療的照護和支持外,社會性的支持也是關注的重點。例如,產房的走道上有一個櫃子,裡面裝滿許多布偶,全是由慈善志工編織和捐贈給醫院,讓流產家庭可以出院時帶回家做紀念。另外,Hvidovre Hospital在兩間產房的外面——休憩區的牆壁上也特別闢出一面「蝴蝶牆」。Louise跟我們解釋,每一隻顏色大小不同的蝴蝶都是流產家庭放上去的,是對寶寶的紀念,也是對寶寶的祝福。讓流產家庭離開醫院後,不會有什麼未了的遺憾。

許多研究指出,經歷流產的女性在失去胎中腹兒後,因為缺乏「 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的歷程,沒有一個轉化生命歷程的儀式,使得他們焦著在過渡時期的閾限情境裡,陷入憂鬱和悲傷。在這兩次所參訪的醫院助產師也都指出,流產家庭在離開醫院前,若能透過一些小小的儀式,像是是讓女性和伴侶寫下對流產的寶寶的話,甚至僅僅只是寫下流產的寶寶的名字或只有他們知道的符號,放在某個他們知道和有紀念意義的地方。透過這個紀念性的儀式,得到一種完整性的告別,爾後能夠邁向下一階段的人生。
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的生命之樹
不同於Hvidovre Hospital,在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的紀念性標誌是在流產產房窗外院子裡的一顆樹,流產家庭可以在木頭做成的小吊牌上寫下想說的內容後掛在樹稍,風吹動時,樹梢上的吊牌會閃閃躍動,和因彼此碰撞發出脆耳聲響。
紀念的構想來自一位流產女性,在院子裡的樹上放上木片,讓流產家庭在離開之前寫上他們想對寶寶說的話、或者寫上寶寶的名字和生日,作為紀念。所以2020年開始,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也在產房旁的花園闢出這個地方,讓流產的女性和伴侶可以在樹上放上木制吊牌,吊牌上可以自由書寫和畫畫。樹上掛滿的木製吊牌,最後也會回歸塵土,成為環境的一部分,寓意著自然與永續。

團體性的哀傷支持
Dorte說Aarhus University Hospital長期關注流產的家庭,所以助產師會在流產女性出院一個月後,安排每個禮拜一次的團體活動。主要是讓這些家庭聚在一起,分享自己的悲傷或者分享生活。每次的活動大概三小時,每個禮拜見一次面,為期六個禮拜。之後各家庭可以自己私下相約聚會,希望讓彼此發展成重要的支持網絡。團體的活動時間不一定是在室內,有時候也會安排室外活動,例如走路的行程。Dorte有特別說,他們的經驗是安排室外的活動讓男性參與者比較願意講話。
完善的孕產照護系統: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與流產照護
丹麥的生育照顧長期以來都是以家庭為單位,即便是流產照護,也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考量和設計。
在這兩趟的特別產房參訪更讓人感受到,流產不僅是一個家庭的事情,也是國家的事情。是一個擁有完善照護系統的國家,在提供孕產照護上應該要有的基本核心價值。因為女性的生育不只是生出活產兒;也可能是生死別離。我們如何承接和照顧這些面對流產的悲傷和失落的家庭?換句話說,國家要如何設計一套完善的生育和流產照護的支持系統?從丹麥的流產照護產房設計學起,這些都是未來台灣相關的孕產政策和醫療照護最佳參考。
本文亦刊載於聯合報副刊:https://reading.udn.com/read/story/7347/8998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