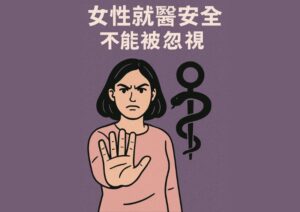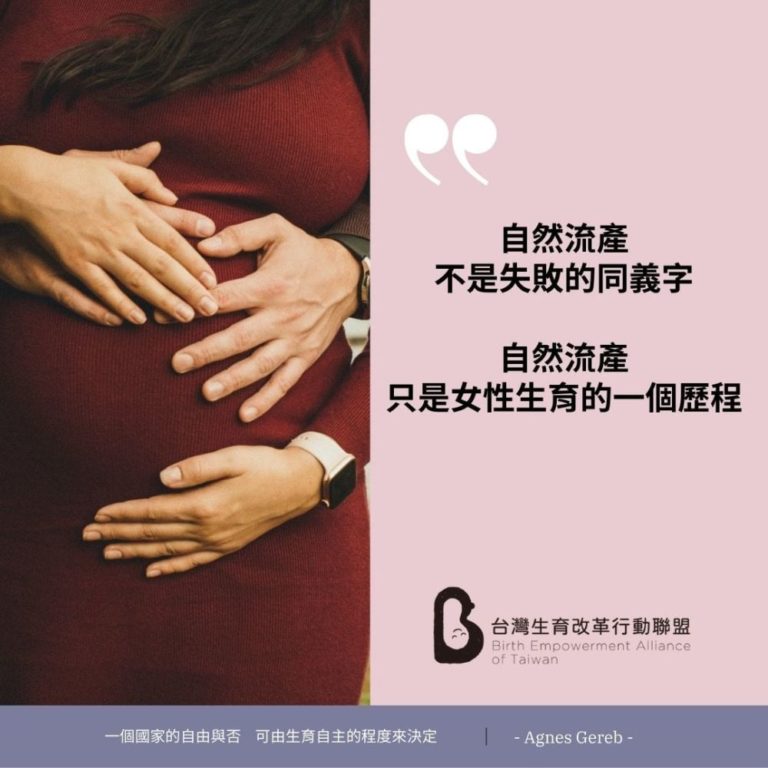「我這輩子最受羞辱的經驗,就是我生孩子的時候。」一位社運界朋友的話,道出了多少台灣女性的心聲?
在婦研縱橫最新一集的podcast中,生動盟資深成員陳玫儀深度剖析:為什麼男性決策者主導的醫療體系,讓女性在產台上失去尊嚴?什麼是「溫柔生產」?生產計畫書為何讓醫界大反彈? 從「母親不服從運動」到「哺乳好自在」,十年倡議路上的酸甜苦辣。
生動盟三個改革目標,翻轉台灣生育文化:
- 不想生的人不被催生
- 想生的人可以好好生,生得像個人
- 生完「同村共養」
當醫療常規遇上性別觀點,會激盪出什麼火花?當生產不再是「疾病」,而是女性的生命禮讚,我們的社會會如何改變?
婦研縱橫EP4|孕產為何需要性別
文字記錄|台大婦女研究室 編輯室(倪紹恩)
受孕、懷孕與生產(簡稱孕產)是女性身體特有的生命活動。孕產過程的種種,可能在女性生命中形成難以止息的餘波。本集節目中,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Birth Empowerment Alliance of Taiwan, BEAT,下稱生動盟)的資深成員陳玫儀,應邀探討性別觀點如何有助於理解生育議題,並分享生動盟多年來倡議「生育自主」的寶貴經驗。
主持人官晨怡首先提到,自己當年因研究主題高度相關而參與了生動盟的創立,期待透過本集節目與老夥伴陳玫儀一同省視初衷和來時路,進而凸顯性別觀點在孕產議題中的重要性。官晨怡認為,由於女性是孕產的主體,因此,環繞孕產而生的經驗、方式與社會期待應亦反映特定的性別關係和想像;然而,臺灣卻較少有人從性別角度關切生育議題。官晨怡問道:「為什麼孕產中一定要談性別?沒有任何的性別觀點及意識,對於孕產會造成何種影響?或是說,如果我們在孕產過程裡不去照顧性別主體時,這對於性別主體的未來或整個社會的性別關係,將造成何種影響?」
性別差異與醫療常規
陳玫儀指出,由於孕產是女性特有的身體經驗,「男性不見得可以感同身受」,因此,應該鼓勵廣大女性「不停述說她的身體經驗,因為沒有人可以代勞,沒有任何一個男性可以這麼精準地把生產陣痛給表達得非常清楚。」孕產婦的感知經驗有其多樣性,有的可能覺得產痛難耐,有的卻沒有同樣劇烈的感受;不論如何,關鍵在於女性應該不斷敘說自身經驗,以增進公眾對於孕產的理解。此外,儘管男性和女性的性徵──以及隨之而來的身體經驗──有所不同,但陳玫儀表示,男性陪產者(例如親密伴侶)的投入對於女性孕產至為關鍵:「就像是運作一家公司一樣,這間公司會因為有你的參與而運作得更好。」即使並非生產的主體,「但男性的參與一樣是重要的」。
官晨怡回應道,探討孕產過程中的性別議題,是為了破除以往不被正視的「權力關係與隔閡」。男性無法理解女性獨有的孕產經驗,可能較難研擬出有效支持孕產婦的方案,卻經常位居決策者的角色(諸如醫師、醫院主管、生產制度的管理者等等),「決定了我們的身體該怎麼樣擺置跟處理」。如此一來,「權力關係跟隔閡相互加乘」,助長了不利於孕產婦的生育模式。
此種生育模式與醫療常規(professional custom)緊密相關。醫療常規,係指一般醫師在臨床現場廣泛從事的醫療方法,亦即醫師之間依其職業上通常之實務運作(ordinary practice)所形成的醫療慣例(陳聰富,2012,頁359)。根據陳玫儀觀察,就制度及結構而言,今日與十年前有關生育的醫療常規「其實沒有太大的鬆動」;常規衍生的迷思至今仍根深蒂固。官晨怡對此表示認同,並指出若要改變一般民眾對生產的既定看法可能相對容易,但是對醫療專業人員來說,常規的鬆動可謂一大挑戰,當現代醫學教育令其朝醫療常規的方向「社會化」以後,「他們就無法再接受其他的方式跟可能性」。這點體現在官晨怡的課堂上。當官晨怡和學生探討醫療常規的必要性,「我經常發現反應最激烈的是醫學背景的學生,他們就會覺得我在講非常危險的事情。」官晨怡表示,即使有些年輕醫師設法引入有別於常規的實踐方式,「但是產房裡頭會有非常多不同的stakeholder(利害關係人),比方說護理師、行政人員、住院醫師、不同層級的醫師,他們也許都會紛紛想要出手制止你。」
陳玫儀認為,對於孕產婦不甚友善的醫療常規,正是削弱女性生育意願的關鍵原因之一。陳玫儀從性別觀點關切孕產議題,得出三個工作目標:「第一,不想生的人不被催生;第二,想生的人可以好好生,生得像個人;第三,生完『同村共養』。」就第一個目標而言,陳玫儀提到由於只有女性具有孕產的生理機能,因此,當社會面臨少子化議題時,「我們常常想的是要怎麼樣讓女人願意生,然後要給什麼樣的補助、多少錢,但是我們常常忘了女性在懷孕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其實跟男性是非常不一樣的。」具體來說,孕期中的女性身心都會經歷「大大小小不同的變化」,凡此變化對於婦女的情緒、身體健康、職業生涯、乃至人生際遇都可能造成巨大影響,而上述體驗對男性而言可能較感陌生。
陳玫儀強調,我們當然需要尊重個別女性的生育意願,但應該進一步思考的問題是:「這些不生的人,是她真的不想生?還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普遍來講對女性不夠友善,以至於她選擇不生?」面對孕產婦的感受、需求和期待,醫療專業人員可能反應消極,甚至在傳統生產過程中施以常規性的過度醫療介入(overutilization),例如禁食、灌腸、剃陰毛、剪會陰等等,對孕產婦的身心造成諸多負面體驗。陳玫儀便舉自己的社運界友人為例,「她只給我一句話,她說:『我這輩子最受羞辱的經驗,就是我生孩子的時候』,這句話的確簡短有力,道出了大部分女性在生產過程當中不被尊重、不被當成一個『人』,好像只是一具『載體』,目的就是把孩子生出來而已,而我本人並不重要。」概括而言,既有生產模式難以有效回應孕產婦的不適感受、需求與期待,導致女性為了維護自身尊嚴而決定「不生」或「生完之後再也不生」。
相較於傳統、常規性的生產模式,「溫柔生產」的實踐值得留意。溫柔生產(holistic birth)的原則在於,充分尊重孕產婦的自主性,協助其了解醫療處置過程並參與決策。陳玫儀便曾公開分享,自己正是受到「溫柔生產」理念啟發,自行擬定「生產計畫書」,與助產師、婦產科醫師基於平等合作關係來協商期望的生產方式,從而獲致一次友善的孕產體驗。[1]
所謂生產計畫書(birth plan),係指促進孕產婦與醫療人員溝通的工具,旨在主動表達孕產婦自身的需求及目標,亦可說明不願採用或期望減少的非必要醫療介入(unnecessary medical interventions)。2014年,任職於婦女新知基金會(下稱新知)的陳玫儀,即發起「母親不服從運動」,向公眾徵求並分享形形色色的生產計畫書,期能在臺推廣這項國外行之有年的產前溝通工具。[2]陳玫儀強調,生產計畫書並無制式範本,甚至可以繪圖呈現,「我們那時候就收集到非常多、我覺得百花齊放的生產計畫書,我們從來沒想過原來可以這樣寫。」除此之外,新知也召開記者會明確呼籲醫療院所主動提供生產計畫書範本、積極與孕產婦溝通生產需求,並進一步訴求衛生福利部在進行評鑑時針對主動提供生產計畫書之醫療院所給予加分鼓勵。[3]然而,此舉激起醫界人士的強烈反彈。同(2014)年7月,台灣婦產科醫學會、台灣周產期醫學會召開聯合記者會,嚴詞駁斥新知的主張,聳動人心的標語寫道:「醫生,我要在廁所裡面生?!」
收到消息,陳玫儀隨即聯絡夥伴前往記者會現場,澄清己方訴求。[4]醫界人士在會中「要求衛福部要辨明當代產科的主流」,直指生產計畫書的範本「完全違反醫療常規,不合常理」,[5]並進一步強調「醫療不應該契約化,萬一發生不可預期的狀況,到底是要照著契約處理、還是醫療專業走,可能讓醫師綁手綁腳。」[6]然而,在陳玫儀看來,對於生產計畫書的倡議,不必然形成忽視醫療專業與生產風險的雙重負面後果。[7]因為生產計畫書並非一紙不可協商的剛性文件,其目的並非要求醫師照章行事,而是在生產這一具有風險、充滿變數的動態過程裡,盡可能維護孕產婦的人權,包括自由選擇權(right to liberty)、身體自主權(right to autonomy),以及追求快樂的權利(right to pursuit of happiness)。
值得探討的問題在於,醫療專業人士對於孕產的醫療化(medicalization)建構是否必要?換言之,懷孕及分娩原本是普通、自然的身體現象,卻逐漸轉變為類似「疾病」、亟需醫學干預的異常問題,此一變化頗值反思。儘管現代醫學的確有助於大多數嬰兒及母親平安度過分娩過程,卻難免導致女性對於她們生命中的關鍵環節──懷孕及分娩──失去控制。孕產婦的意見和知識在專家眼中可能無關緊要。
上述爭議凸顯了現代醫療專業社群高度重視常規的保守傾向。然而,孕產婦應為有權獲得充分資訊後自主選擇的主體,而非以被動姿態亟待醫師救治的「病患」。面對看似牢不可破的生產常規,陳玫儀樂觀以待:「一個議題,其實你都不要去想說十年它就可以改變,它可能是需要透過好幾個世代慢慢改變。我覺得如果可以在我們這個世代,慢慢鬆動一點點,它總是有被鬆動的一天,不過就是需要有人持續地敲磚。」因此,陳玫儀認為生產常規仍有轉變的希望,「不過我們就是得嘗試不同的運動策略。」
多元的改革行動
陳玫儀回顧過往,在生動盟正式成立(2014年)之前,[9]旨在建立友善孕產環境的社會改革便已展開。適逢生動盟成立前後,陳玫儀任職新知期間,除了上述的「母親不服從運動」外,亦籌辦了題為「哺乳好自在」的活動(2013年),向公眾徵求哺乳影像。陳玫儀解釋,「哺乳好自在」緣起於一則時事新聞:2012年,一位婦女正在國立故宮博物院的一樓展覽室外哺乳,工作人員卻以「妳這樣非常不雅觀」為由,要求她遷往位於地下室的哺乳室。[10]然而,根據《公共場所母乳哺育條例》,即使公共場所已設置哺(集)乳室,婦女選擇母乳哺育場所的權利依然不變,「任何人不得禁止、驅離或妨礙」。該工作人員與故宮負責人因此遭罰。
陳玫儀表示,這起新聞「讓我很生氣,我覺得大部分人都誤解了哺乳室的真正用意,它不是要把媽媽關在一個不被人家看見的空間裡進行哺乳,而是讓不想在公開場合哺乳的媽媽有另外的選擇。」新知因而在隔(2013)年策劃「哺乳好自在」活動,徵求婦女於公共場所母乳哺育的平面影像照片。宣傳語如此寫道:「沒有人可以要求我們應該回家、應該躲在哺乳室或是穿上哺乳巾。因為哺乳不是色情,無關裸露,更不會有礙觀瞻。」[11]陳玫儀提到,自各方蒐得的哺乳影像最終拼成一幅臺灣地圖,藉此表達「臺灣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自在哺乳」的意象。
2014年生動盟成立以後,長期發展具備性別關懷的產前教育及產後支持服務。其多元的活動和課程不只以女性為主體,亦觸及同志伴侶的需求。陳玫儀指出,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同家會)的課程合辦經驗,有助於理解孕產需求的多樣性:無論在異性戀家庭與同志家庭之間,或是在男同志與女同志之間,均呈現同中有異的現象。此亦進一步促使生動盟思考「如何為同志家庭提供支持服務」,例如,實務上應敏感於可能鞏固刻板印象的詞彙。據陳玫儀轉述,現任生動盟常務理事的鍾秀靈,也是一位國際認證泌乳顧問(International Board Certified Lactation Consultant, IBCLC),曾特別提醒道:「生產教育常常會講說,小孩抱久了會有『媽媽手』[狹窄性肌腱滑膜炎],但我們也要注意,其實男同志會有『爸爸手』。」向同志家庭提供支持服務時,亦無須打探懷孕的細節,或無謂地詢問:「你們兩個誰扮演媽媽的角色,誰扮演爸爸的角色?」因為服務的關鍵在於如何協助對方「步入育兒的生活」。
除了服務於同志群體的親職課程,生動盟也規劃面向兒童的活動。陳玫儀提到,有鑑於兒童可能經由母親、電視、電影等媒介,從幼時起便形成諸多圍繞生產的負面印象,故而期待藉由友善生產教育及身體教育,「讓孩子去理解,生產這件事情不應該這麼可怕,因為你應該要得到很大量的支持跟協助。」另一方面,生動盟也透過自然流產等涉及生產風險的課程內容,切實、平衡地向孩童呈現孕產的多面性。對於生動盟長年且多元的實踐,官晨怡深感驚豔與自豪:「這些都是其他NGO不會想到的方向和做法,而生動盟不但想到,還付諸行動」,這些實踐可謂是生動盟扎根於性別與孕產議題後所長出的美麗分支和成果。
回首來時路,陳玫儀在投入倡議的過程中因緣際會結識許多同伴,包含作家、醫療記者、紀錄片導演、研究孕產的學者等等。正是藉由一次次的倡議,四面八方各有所長的人士,早在生動盟成立前便陸續相遇相知,直到2018年正式立案為人民團體時,關鍵的工作夥伴「就到位了」。陳玫儀以「捲動」意象生動描述此一集結歷程。經過生動盟多年的推廣,陳玫儀認為有越來越多專業人士「被捲入」生產改革倡議,例如有瑜珈教師受到啟發、嘗試專為孕婦設計課程等等,他們貢獻所長、致力發想多元的服務方案。這些多元的實踐方式也成功轉變某些婦女對於孕產的負面觀感與生產創傷,讓她們「覺得原來生孩子這件事情沒有想像中那麼可怕」,甚至樂觀看待「再生一胎」的可能性。陳玫儀總結道,討論孕產議題之所以需要性別觀點,是因為「我們希望每一個願意生養孩子的家庭或個人,都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顧──不論你是什麼人。」
節目文字記錄:https://gender.psc.ntu.edu.tw/fwgs_podcast_ep04/
收聽節目
- Spotify:https://tinyurl.com/yow6gdch
- Apple Podcast:https://tinyurl.com/ytfnl8ae
- SoundOn:https://tinyurl.com/yvbqp2m3
- KKBOX Podcast:https://tinyurl.com/yv25t3pp
- YouTube:https://tinyurl.com/younvrnq